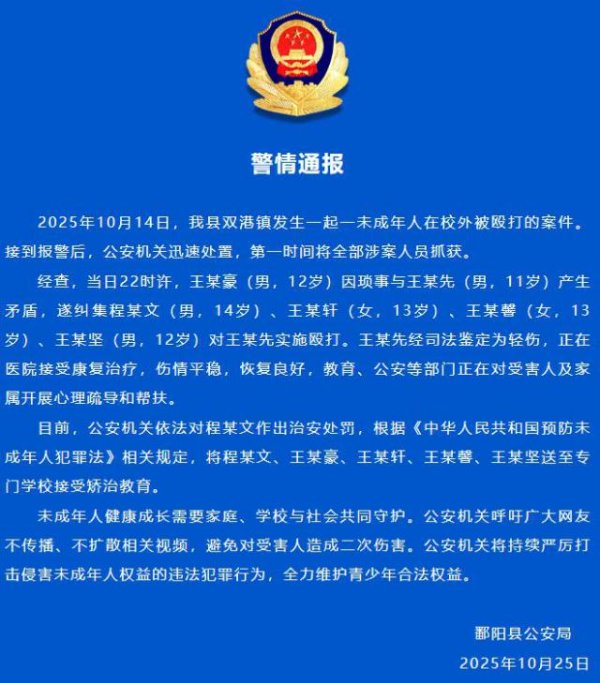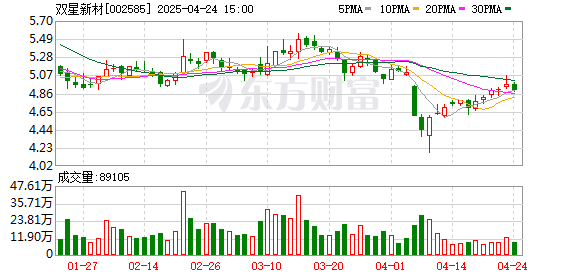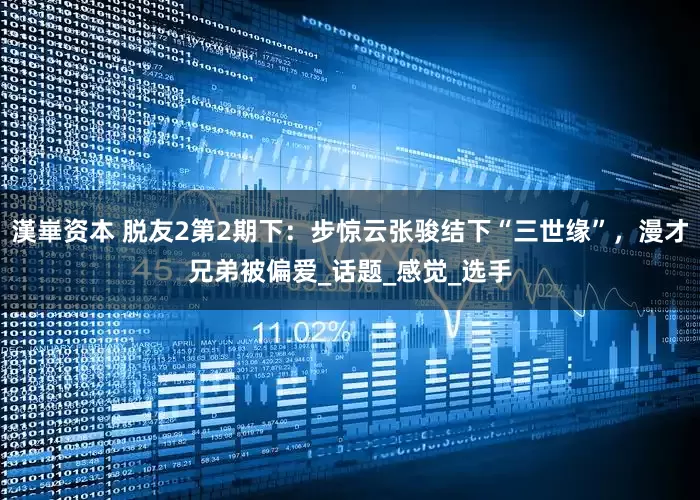《卢旺达饭店》
他是用肉身与世界碰撞的先行者,在四十余年的驻外记者生涯中,足迹遍及全球一百余个国家,曾亲历二十七场革命和政变,亲临火线带回一手报道;他以深沉的目光注视历史,用柔软的心感知他人命运,用简洁有力的文字搭建起文明间的桥梁。
他就是20世纪波兰新闻和文学界里程碑式的人物雷沙德·卡普希钦斯基,这位曾六次提名诺奖的“世纪记者”活成了20世纪新闻界的一则传奇。
今天,要想了解20世纪的强权与战乱,俯瞰复杂的苏联帝国、深入光怪陆离的非洲族群与文化,我们须得跟随 卡普希钦斯基的足迹,在他的作品中重新走入那段漫长而复杂的人类历史。
作为了解苏俄的必读之书,《十一个时区之旅》记录下了卡普希钦斯基横跨苏联十一个时区,穿越整个苏联的广袤地域,走遍十五个加盟国的旅程,呈现了一个真实、复杂、充满矛盾的超级大国;
展开剩余92%《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》记录下了卡普希钦斯基对异域与他者的觉醒之路,正是在旅程中他发现了自己一生的志业——前往罕有人至的遥远角落,理解和讲述世界的多样性,在参差多态的现象中寻找普世真理;
而《太阳的阴影》记载了卡普希钦斯基在30多年间深入非洲大陆的所见所闻,书中展现了最真实的非洲图景:那里有仿佛世界诞生之初的极致美景,同时也是无数部落、民族、文化和势力交织的汹涌之海。
“不同的文化就像一面镜子,我们可以从中审视自己,以更好地了解自己——每个早晨,锲而不舍,一次又一次地踏上旅程。”
独家加赠大象出发行李牌
精彩好书,不要错过❗️
01
非洲
我在这里已经一个星期了,试图了解阿克拉。这座城市就像是从灌木丛和丛林中爬出来的一个小镇,经过不断的自我复制与过度扩张,最终停在了几内亚湾的海岸边。阿克拉是平坦的,大多是简陋的低矮平房,偶尔有两层以上的楼房。这里没有复杂的建筑风格,没有奢华和排场。普通的灰泥墙,墙面是奶油色、浅黄和浅绿。墙上布满水痕。雨季刚刚过去,留下了无尽的斑点、马赛克、奇异地图和繁复花纹组成的星空图,如同抽象的拼贴画。市中心的建筑很紧凑,车水马龙,人声鼎沸,而生活就在街头上演。街道是车行道,两旁是露天的排水沟。没有人行道。汽车和人群混杂在一起,行人、汽车、自行车、手推车,还有牛和羊—所有的东西都一起流动。沿着整条街道的两边,在排水沟的后面,家庭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场景正在展开。妇女们在捣木薯泥,在炭火上烤芋头,煮着各种食物,兜售口香糖、饼干和阿司匹林,洗衣服并晾晒。仿佛有一条规定,要求所有人早上八点必须出门,待在街上。实际原因并非如此:房子太小了,破旧又拥挤。室内没有通风,空气滞闷,气味也难闻,几乎无法呼吸。此外,待在街上还可以参与社交生活。妇女们不停地交谈,喊叫,手里比划着,放声大笑。站在锅盆旁边,她们有绝佳的观测点,可以看到邻居、行人、整条街,听到争吵和闲话,关注正在发生的各种事情。一整天,人们都在人群中活动,呼吸着户外的空气。
-
库马西坐落在绿树和鲜花之间,位于平缓的山丘上,就像一座巨大的、允许人们定居其中的植物园。这里的一切似乎都对人类充满善意——气候、植物,还有这里的人。 清晨虽然只有短短几分钟,但却美得令人惊叹。周围一直是黑夜,忽然间,太阳从里面游了出来。游?这个动词似乎暗示着某种缓慢的过程。 但实际上,太阳就像一颗球被人从山后猛地抛出。你立刻看到那团火球,它离你那么近,甚至让人感到一丝恐惧。而且这团火球还在朝你移动,越来越近。
太阳的出现就像发令枪,整个城市即刻开始运转。仿佛人们整夜都蹲守在他们的起跑线上,现在太阳一声令下,他们立刻迈开脚步,奔向前方。没有任何过渡阶段,也没有准备时间。街上顿时挤满了人,商店开门,篝火和厨房冒出炊烟。
《镜子》
黑夜降临是非洲人最愿意聚在一起的时候。没有任何人想在这时候自己待着。自己?这代表了不幸,是来自地狱的惩罚!这里的孩子们也不会早早睡觉。全家人、全氏族、全村人——所有人要一起踏入梦乡。
我们开车穿越乌干达的时候,这个国家已经在夜的窗帘后沉沉睡着。维多利亚湖应该就在附近,还有安科累王国和托罗王国、穆本德的牧场、默奇森瀑布,应该都在附近。这一切就像煤渣般沉淀在黑夜的底部。夜晚寂静无声。汽车的前灯深深地穿透了黑暗,一群疯狂的苍蝇、马蝇和蚊虫在光芒中旋转飞舞,它们不知从哪儿突然冒出来,在短暂的一瞬间,在我们眼前演绎它们生命的角色:昆虫狂舞,然后被疾驰中的汽车的前盖无情地撞碎。
-
埃塞俄比亚中部是广袤的高原,无数悬崖和峡谷纵横交错其中。雨季时,湍急的河流沿着这些深谷流淌。其中一些到了夏季会干涸,消失,露出干裂的河床信汇网,风在上面扬起黑色的尘土——被太阳烤干的泥浆。在这片高原之上,时而会有三千米高的山峰兀自突出,但它们与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脉、安第斯山脉或喀尔巴阡山脉却毫无相似之处。这些高山由风化的石头组成,呈铜褐色,山顶平坦而光滑,甚至几乎可以当作天然的机场。乘飞机从这些山峰上飞过,可以看到建在上面的没有水源和电灯的简陋茅草屋和泥坯屋 。你立刻会想到:那里的人怎么生活?靠什么生活?他们吃什么?他们为什么要待在那儿?正午时分,在这样的地方,大地的温度一定就像滚烫的煤渣,灼烧他们的脚,把一切都变成灰烬。
-
傍晚时分,我们一同坐在大树下,一个姑娘递给我一小杯茶。我听着这些人的讲述,他们坚毅的面庞闪着光芒,如同乌木雕刻而成,融入了静止的黑暗之中。我不太能听懂他们说的话,但他们的声音是那么的严肃认真。他们在说话的时候,认为自己是要对本民族的历史负责的。他们必须将历史完整保留并继续发展。没有任何人能说“你们去读一读关于我们历史的书吧”。因为从没有人写过这样的历史书,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书。除了现在在这里讲述的历史,其他历史都不存在。这里永远不会出现欧洲那种“科学历史”或“客观历史”,因为非洲的过去没有文件或记录,每一代人都是一边听着别人传授给他的版本,一边对这个版本进行修改,不断地改变、转变、修订和修饰它。 但正是通过这种方式,历史摆脱了档案的沉重,摆脱了数据和日期的严格要求,历史在这里呈现出最纯粹的、如水晶般晶莹剔透的形式——神话。
——《太阳的阴影》
《卢旺达饭店》
02
印度
我听从了接待员的建议,乘公共汽车前往贝拿勒斯。车子驶过贾穆纳河和恒河的河谷,驶过平坦、绿色的乡村,其间点缀着农民的白色身影,他们在稻田中涉水,用锄头挖地,或是头上顶着包袱、篮子或麻袋。但窗外的景色不断变化,眼前常常是一片广大的水域。这是秋汛的季节,河流变成宽阔的湖泊,变成好一片海。岸边有赤脚的灾民扎营。他们在水上涨前撤离,但仍住在水边,只离开必要的距离,一旦洪水后退就立即返回。在行将结束的日头那巨大热浪的辐射中,水蒸发了,乳白色的、静止的雾气笼罩在一切事物之上。
我们抵达贝拿勒斯时天色已晚,夜幕已经降临。这座城市似乎没有郊区,而郊区通常会让人来到市中心之前有所准备;在这里,人们突然就从黑暗、寂静和空旷的夜色进入灯火通明、拥挤喧闹的市中心。为什么这些人蜂拥而至,挤挤挨挨,而明明在旁边就有那么多的空地,能容得下每个人?下车后我四处走了走。我到了贝拿勒斯的城乡交界处。在黑暗中,一边是寂静无人的田野,另一边是城市的建筑,人口密集,熙熙攘攘,灯火辉煌,嘈杂的音乐声此起彼伏。我无法理解这种对拥挤生活的需求,对摩肩接踵的需求,对无休止的推搡的需求—尤其是那边不远处就有那么多空地。
当地人建议我夜里不要睡觉,这样我就可以在天还黑的时候到恒河岸边,在河边的石阶上等待黎明的到来。他们说:“日出非常重要!”声音里回荡着对真正崇高事物的期待。
当人们开始聚集在河边时,天确实还很黑。单独的,成群的。整个家族。朝圣者的队伍。拄着拐杖的瘸子。瘦骨嶙峋的老人,一些被年轻人背着,还有一些—扭曲、疲惫 —靠自己在柏油路上艰难地爬着。牛和山羊跟在人们后面,成群的消瘦病弱的狗亦是如此。我也加入了这场诡异的神秘剧。
走到河边的台阶并不容易,因为那前面是狭窄、憋闷、肮脏的小街,挤满了乞丐,他们没完没了地纠缠朝圣者,同时发出令人难以忍受的可怕而刺耳的哀鸣。最后,经过各种通道和拱廊,人们出现在直达河边的台阶顶端。虽然天还没亮,但成千上万的信徒已经在那里了。有些人兴致勃勃,挤着往前走,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往哪里挤,出于什么目的。另一些人以莲花式打坐,手臂伸向天际。台阶的最下面被那些进行净身仪式的人占据着—他们蹚进河里,有时会把自己完全浸入水中。我看到一家人正在为肥胖的祖母进行净身仪式。老奶奶不会游泳,一下就沉到了
水底。家人冲了过去,把她带出水面。老奶奶大口大口地呼吸空气,但他们一松手,她就又沉下去了。我可以看到她鼓起的眼睛,惊恐的脸。她再次下沉,他们再次在浑浊的水中寻找她,再次把她拉上来,她已经奄奄一息了。整个仪式看起来就像酷刑,但她没有反抗地忍受着,或许还心怀狂喜。
此时的恒河辽阔宽广,水流缓慢,边上是一排排的木柴堆,上面燃烧着几十、几百具尸体。好奇的人可以花几卢比坐船去这个巨大的露天火葬场。赤着膊、满身烟灰的人在这里忙碌着,还有许多年轻的男孩。他们用长杆调整柴堆,以便气流更通畅,使火化更快进行;尸体的队伍没有尽头,得等待很久。敛尸工将仍在发光的灰烬耙开,推进河中。灰色的骨灰在水波上漂浮了一会儿,但很快,被水浸透,就沉入水中,消失不见了。
——《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》
《上帝之城》
03
沃尔库塔
沃尔库塔位于科米共和国,在北极圈内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,这里发现了大量煤矿。一个煤炭工业区迅速形成,其建造者主要是囚犯,恐怖政策之下的受害者。几十个劳动营拔地而起。很快,沃尔库塔就像马加丹一样,成了一个象征,一个唤起忧惧的名字,一个可怕的、往往是有去无回的流放之地。为之添砖加瓦的,还有NKVD的穷凶极恶,煤矿中致命的劳役、导致囚犯大量死亡的饥饿,还有噩梦般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寒冷。这里的酷寒折磨着手无寸铁、衣不蔽体、长期挨饿的人们,耗尽他们的忍耐力,让他们成为最残忍的折磨的牺牲品。
如今,沃尔库塔仍然是一个煤炭工业区,由十三座煤矿组成,它们沿着城市形成一个大圆环。每个煤矿旁边都有一个矿工定居点,其中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劳动营,现在仍然有人居住。定居点和矿井之间通过一条环形公路相连,两路公共汽车在上面相向而行。汽车在这里仍是稀罕物,所以公共汽车是唯一的交通工具。
就这样,我坐上其中一路公共汽车,去拜访热纳季·尼古拉耶维奇,我只知道我要找“共青团波西奥莱克”,6号屋。一个小时后,司机停在一个应该是共青团波西奥莱克站的车站,打开车门,给我指了指要去的方向。但他指得很模糊,几乎可以理解为朝着银河系数百万颗星星中的任何一颗走去。但他的模棱两可并没有带来什么后果,因为一下车,我很快就迷失了方向。
起初,我发现自己站在一片漆黑中,什么也看不见。视力逐渐适应黑暗后,我发现周围是积雪覆盖的山丘。强风每隔一会儿就会吹袭山巅,把大片的雪花掀向天空,仿佛山顶上喷发出白色的岩浆。到处都是“雪山”,没有灯光,没有人烟,我冷得无法呼吸,一呼吸肺部就会剧烈地疼痛。
《雪人》
自我保护的本能告诉我,要摆脱这种局面,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要离开车站,要等下一班公共汽车来,它迟早会来的(虽然时间已经过了午夜)。但我的本能让我失望了,于是,在某种致命的好奇心的驱使下,或者仅仅出于轻率,我开始寻找共青团波西奥莱克和6号屋。轻率之处在于我没有意识到,身处北极圈的夜晚、身处白雪覆盖的荒原、脸冻得生疼、几乎无法呼吸,这一切意味着什么。
我径直向前走,不知道身在何处,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。在某一刻,我看到前方有一个深坑,深坑底部有一栋木制的平房。我滑了下去,沿着结冰的山坡滚了一段路。那是一家商店,门锁着,上着木栅栏。这个地方看起来安静而舒适,我甚至想在这里住下来了,但极地探险家的警告浮现在我脑海中,他们说,在冰天雪地的荒原里,这样一个温暖的雪凹就意味着坟墓。
我已经快没力气了,但仍时不时振作起来再走几步,就在这时,我看见一个女人的身影,她正在狂风中挣扎,弯曲着身子,弓着背。我拖着身体走向她,气喘吁吁地说:“6号屋,”然后又说,“6号屋。”声音里充满希望,好像我的全部救赎都藏在这个地址中。
“你走错方向了,师傅。”她大声喊道,好盖过风的声音。“这是去矿井的方向,你应该……朝那边走。”她也像公共汽车司机一样,用手指了指银河系数百万颗星星中的一颗。
“不过我也要去那里,”她接着说,“走吧,我带你去。”
——《十一个时区之旅》
《雪人》
“世纪记者”雷沙德·卡普希钦斯基
20世纪波兰新闻和文学界里程碑式人物
曾亲历火线与政变,以肉身碰撞世界
用文字记录真实的历史与复杂的人性
最终搭建起文明的桥梁
独家加赠大象出发行李牌
精彩好书,不要错过❗️
🎁
🎁
发布于:北京市鼎盛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